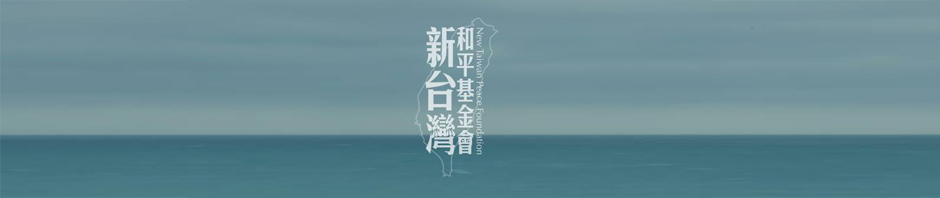2022年3月8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轉型正義系列講座第三場:「告密者、我和我的被監控檔案」,邀請立法委員、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老師蒞臨演講。
范雲老師於演講一開始回憶閱讀自己被監控檔案紀錄的心情,當她知道自己學生時代竟被嚴密監控時,相當驚訝。大學時代的范雲,積極推動校園學生自治的活動,也加入大陸社等異議性社團,當時台灣剛剛解嚴,正好是她大一暑假的時候,那時候校園中戒嚴的氣氛逐漸淡去,不覺得身邊會有所謂的「告密者」。對她來說,那是一段美好奮鬥的歲月,從來就沒想過身邊的同學或運動夥伴,可能就是監控她的人。
【看完被監控檔案在淚水中醒來】
范雲開玩笑表示,最初閱讀自己的監控檔案時,第一個想法是:許多年輕時代曾經付出努力的事情,現在早已經忘記,幸好有人這麼仔細地幫你記錄下來;原來當年自己那麼厲害,有這種論述能力,她也自謙地說,為什麼往後二、三十年都沒有進步。
然而,范雲也談到,監控檔案對於當事人帶來心理上的折磨。當她看完檔案後的那一晚,徹夜輾轉難眠,腦海中不斷猜誰可能是監控者;好不容易睡著,卻在淚水中醒來,深深覺得自己被背叛了。
一切回溯到范雲從范雲教授進到立法院工作,成為范雲委員之後,開始認真推動轉型正義的議題。
最初,范雲覺得,所謂的「受害者」,應該是像陳文成、林義雄那樣付出慘烈犧牲,或是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有一天,她接到台大社會系的同事、也是促轉會檔案公開計畫的執行者的林國明教授通知她,最近發現的一批檔案裏面,有她的「專卷」。
當時范雲還不了解「專卷」意味著什麼,經過林國明教授說明後才知道,當時國民黨及政府機關進行校園監控,都是以專案的形式,以學校或學生社團為單位的形式,進行情治工作,令人意外的是,在專案之下,范雲老師是特別被單獨監控的對象。
范雲積極參與社團和學生會活動大約是在1990年左右,而據促轉會調查顯示,專門針對學生的專卷檔案,大概到了1986年之後就很罕見,可見情治單位當年對她多麼提防。
【范雲的告密者 現居司法體系的高位】
范雲表示,對她個人的專卷監控,直至1994年3月19日才解除,在她的個人專卷中記錄,因為1992年修正刑法第100條後,政府不再懲治台獨思想犯或所謂「分離主義者」,情治單位研判她雖然支持台獨,但是無「暴力台獨」傾向,沒有繼續對她進行監控,蒐集不法事證的必要。
不過,即使1992年刑法由100條修正後,從目前已知的監控檔案,一直延續到1998年8月,也就是范雲出國留學前,都還有文字紀錄。
除此之外,范雲本人也證實,透過閱讀檔案資料可以發現,當年臺大校方、教育部、國民黨和情治系統,彼此之間互相聯繫,共同對她以及其他學生執行監控工作。
有關誰是「告密者」的問題,范雲老師表示,經過資料比對,她有95%的信心,可以確定部分的告密者是誰。
在監控檔案中,紀錄了當時一些參與人數很少的內部工作會議,透過出席者的交互比對,有一些人名重複出現的機會很高,因此可以合理推斷,那些人很可能就是監控工作的協力者或者告密者。其中,有人目前正在司法體系服務,位居高位。
在活動前的提問中,有不少參與者詢問,范雲作為被監控者,對於告密者有什麼看法?對此,范雲提到,如果這些人願意向她承認所作所為,並且真誠道歉,她完全可以原諒他們。然而,直至目前為止,無論是加害者,或者協力者,都還沒有人向她致歉。
【侵害人權的高官 必須自我揭露】
另一個大家感到好奇的問題,到以是什麼原因,讓大學生願意當「抓耙子」?協助情治單位監控自己的同學?
范雲分析,主要還是金錢利益。在閱讀檔案的過程中發現,監控者可以從情治單位、國民黨或教育部收工作報酬,其金額一個月竟然高達18,000元。
當時,大學生擔任家教一個月所得大約3,000元,擔任助教一個月約4,000元,因此,18,000元對學生而言是一筆暴利,具有很強的誘因;由此可見,威權體制為了對付異議者耗費鉅額社會成本,最令人憤怒之處在於,國民黨政權為了維繫統治,不擇手段利誘年輕心靈,讓涉世未深的學生,加入黨國監控體系。
有關轉型正義議題中,對於「加害者責任追究」的看法,作為一位立法委員,范雲主張,就算沒辦法以司法程序對加害者進行法律上究責,但是「道德究責」仍有必要。政府應該公開揭露加害者或協力者的姓名,讓他們受到輿論的道德責難。
特別是過去曾侵害人權的加害者、協力者,尤其公務體系一定層級以上,具有相當決定權的官員,或者國安、情治單位內主導計畫的人士,應該透過修法或立法,揭露這些人過去侵害人權的行為,或者要求他們應當自我揭露。
范雲認為,就連自己擔任立委,民意代表被課以財產申報的義務,難道人權比財產更不重要嗎?同時,政府也應該對於自我揭露設計查核機制,如果有人遭檢舉未誠實揭露,那未誠實揭露的人就要依法給予懲罰。范雲認為,透過除垢與揭露,才能讓台灣人更信任目前的民主體制。
【有不義遺址 卻沒有不義之人?】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目前轉型正義的執行,政府認定了許多當年黨國體制用於關押、審訊或處決政治犯的「不義之地」(不義遺址),卻從來沒有認定一個「不義之人」。
在座談的提問階段,人權運動者艾琳達表示,政治檔案的內容不可盡信,因為有一些線民為了討好上司,寫得很誇張、不符實情。
艾琳達也表示,有一些早期在情治單位從事監控工作的人,在不清楚工作內容的情況下,進到情治單位工作,後來對工作內容很反感就離開,甚至比很多沒有待過情治單位的人還厭惡那裡。由此可見,我們很難以一個人是否曾經擔任線民,判斷他後來的作為是否比較傾向罔顧人權,而在往後擔任公職的時候被揭露。
對此,范雲以林國明教授曾在立法院轉型正義的公聽會上分享的研究成果作為回應。透過審議民主式的討論會議,各種背景與政治立場的參與者,經過理性思辨後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向受到監控的當事人揭露政治檔案。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真相比和解更重要」,這個看法具有很高的社會共識。
【不能為了和解 放棄追求真相】
范雲認為,不能光為了達成「社會和解」,卻連「追求真相」都放棄了。另一方面,真相揭露有層次之分,是一個蠻細緻的問題。
例如,東德的史塔西檔案要開放前,他們對隱私怎麼保障討論了非常多;涉及個人隱私的部分,當事人可以選擇不要被揭露;監控檔案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看,除當事人之外,只有研究者提出申請獲得許可後,才可以觀看檔案。
針對檔案紀錄內容可能有錯誤的問題,范雲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因為檔案的內容不可能絕對正確,但錯誤的比例相對有限,而且可以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與第一手資料之間互相比對,加以確認檔案內容的正確性。
關鍵在於,唯有資料公開,研究者才有辦法以學術標準嚴謹比對、分析,盡可能拼湊出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面貌;透過檔案公開,當不同歷史觀點之間互相衝突的時候,我們得以依據檔案資料尋找事實基礎,進行不同觀點之間的理性辯證,進而釐清事實真相。
★記錄∣台灣新憲青年陣線 林謙